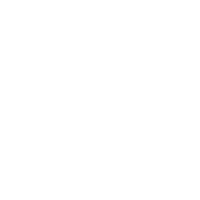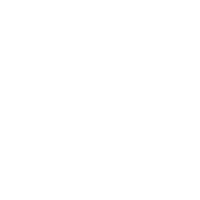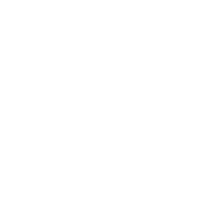工伤认定
工伤行政确认案证据的裁量和证明标准
本案是一起对劳动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是个人行为还是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和不可逆性,案件事实在客观上不可能重现,因此在诉讼中法官要借助于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得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重现,从而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判决。
(一)双方的举证情况
本案中对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目的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有:一是被告劳动部门提交的一份书证和三份证人证言,该证据均为公司在行政程序阶段向劳动部门提供。其中书证是宋德鸿在2003年7月份写的个人总结,从总结可以看出,宋德鸿仅总结了其从事的销售工作情况。三份证人证言是当时在场的公司的三名工作人员出具,证明当时经理让韩某去买水,宋德鸿也在现场并提出和韩某一起去,经理让韩某去叫司机门某,但当韩某和门某下楼时车已经开走。二是原告宋德鸿的法定代理人在诉讼阶段提供的一份书证和一份证人证言。书证是宋德鸿的一本日记,日记中多次记录了宋德鸿为经理李刚开车的经历。证人证言是由宋德鸿当时在公司的同事出具,证明因宋德鸿有驾驶执照,所以跟随经理李刚跑业务并为其开车。
(二)对原告行政程序中未提交而在行政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应否采纳
宋德鸿法定代理人为证明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系履行职务行为而提供的两份证据均系在行政诉讼阶段提供,在行政程序阶段并未提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原告依法应当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证据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经审查,本案中,宋德鸿的法定代理人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劳动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一次性向其告知了申请工伤认定应提供的有关材料,即需要提供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和医疗诊断证明。原告按要求向劳动部门进行了提交。但劳动部门在对用人单位进行调查时,用人单位提出了宋德鸿驾车外出系个人行为的抗辩理由并提交了有关证据。劳动部门采信了用人单位对该事实所举的证据并作出了非因工受伤的认定。即劳动部门在用人单位对原告受伤原因的陈述与原告主张不一致的情况下,并未就该事实进一步向原告进行核实,从而导致原告在行政程序阶段错失了就该事实的举证机会。由此可见,原告未能在行政程序阶段提供以上证据是由于劳动部门执法程序上的缺陷造成的,并非《证据规定》中规定的“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的情形。
另外,工伤行政确认案件有其特殊性,申请人出于治疗、救助的原因,对及时享受工伤待遇有较强的急迫性,所以一般不会存在行政程序阶段故意不提交,而等到诉讼阶段提供证据的可能性。所以对于申请人诉讼阶段提供的证据,应当慎重对待,具备了证据“三性”要求的,法院一般应作为有效证据采纳使用。
(三)证据认证中的法官心证
虽然诉讼过程是一个发现、收集、运用证据的客观活动过程,但判断证据、认识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本身却是主观活动过程。法官在个案中应当根据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对各种证据证明力作出判断,并以此探求实质事实,因此强调法官内心确信的自由心证制度更代表了法律的现实和发展方向。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即明确规定了应当“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审查证据。所以在法律就证据的证明力没有进行预先设定的情况下,法官在调查和辩论的基础上,按照经验法则和逻辑要求,合理地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本案而言:
首先,应当对原告提供的书证——日记本的真实性作出判断。经审查,该日记中记录了原告上学期间及工作后较长一段时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从日记内容上看,有对生活琐事、个人情绪的记录,也有对日常开销情况的记录,宋德鸿本人现在的状况是颅脑一级伤残,故伪造日记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根据生活经验,我们内心应当能够对该日记的真实性予以确信。
原告的举证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证明目的呢?原告提供的日记和证人证言,均不是对案发当日情形的证明,但这两份证据却能够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宋德鸿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经常为经理李刚开车。那么存在这个事实,就为本次宋德鸿驾车外出亦是基于经理指派或履行职责为目的提供了一种可能。结合被告举证的原告写的个人工作总结和庭审中公司经理的陈述,我们了解到,原告被公司录用不足两个月,工作中积极上进,而经理的车平时除了经理使用,并不允许员工使用,且该车仅有一把钥匙。《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那么公司的举证能否达到否定该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呢?
(四)用人单位的举证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一般来讲,确立某类案件的证明标准通常应考虑的因素包括:一是案件的性质,涉及的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涉及人身权利的,应设定比较高的证明标准。而工伤认定案件带有很大人身权的性质。二是案件一旦认定错误可能带来的成本大小。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人没有认定为工伤,那么这个职工可能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造成人身和精神的损害,这种损害甚至将影响其今后的生活。而不应认定工伤的人认定了工伤,企业可能因此造成一定经济损失,而经济损失恢复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人没有认定工伤,带来的成本损失要相对大得多。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对用人单位举证标准的要求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公司提供的几份证人证言可以证明以下事实:经理李刚未安排宋德鸿出去买水,但宋德鸿曾主动提出去做这件事,且宋德鸿将车开走。但公司未能对以下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和举证:宋德鸿是如何从李刚处取到的这仅有的一把车钥匙,宋德鸿“擅自”驾车外出后,在场的公司经理及其他工作人员有无采取有关措施告诫或阻止宋德鸿。如果对以上疑问公司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并举出相关证据,我们有理由对公司主张的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仅为个人行为的主张存在合理怀疑。
在行政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运用要求法官在衡量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根据现有的案件证据考量,行政人员是否形成一种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内心确信而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判断。若存在合理怀疑,应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裁决。就本案而言,公司在行政程序阶段的举证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故对劳动部门认定的宋德鸿此次驾车外出系个人行为的事实应认定证据不足。





 冀公网安备13010202003181号
冀公网安备13010202003181号